一位坚守二十二年的考古队长,于夯土与星象间,揭开人类最早观象台的谜题;一位考古技师,用画笔与手铲,破译藏在“彩绘漆木杆”里的“地中”密码;一位土生土长的襄汾老者,在祖辈相传的“尧窝”与“蛇馍馍”里,读懂了文明基因的流传;一位年轻的考古人,接过前辈的手铲,在坚守中续写“最初中国”的探索篇章……
7月1日,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仪式举行,4位与陶寺有着不同“牵绊”的考古人、学者现场讲述“我和陶寺的故事”。他们的故事,是陶寺从沉睡到苏醒的见证,是文明从传说到信史的实践。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讲述,走进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,共赴一场文明探源之旅。
叩问大地,也仰望星空

何努曾任陶寺考古队第四任队长,二十二年光阴里,他扎根这片黄土,亲眼见证陶寺从麦浪起伏的田野里一点点苏醒,重现四千年前王城的恢宏气象。
在何努看来,陶寺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陶寺观象台——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,它不仅定义了春分秋分、夏至冬至,更精准观测着二十个节令,是陶寺先民仰望星空、丈量时光的旷世杰作。
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绝非坦途。2002年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启动。那年春天,何努接过领队之责。
文献中记载,“尧都平阳”在临汾一带,《尚书・尧典》的满篇星象历法,让何努深信这片土地下必定埋藏着观象的殿堂。
可它究竟在哪里?他们决心有目的地寻找。当时陶寺已确认早期和中期的王族墓地,但墓地附近的三角形区域,始终找不到方向确定其用途:在这片遗址平面上,13个夯土块呈弧形整齐排列,组成半圆环形夯土台。经过分析认为,这些夯土块是遗址柱基,推测原先这里是石柱建筑。可它们究竟有何用途?是房屋、墙垣,还是另有玄机?困惑如迷雾笼罩着众人。
何努想到了好友武家璧,兼具考古与天文学知识的他或许能解开谜题。他将勘探情况和平面图发给武家璧,提出猜想:“这会不会与东边的塔儿山有关,用于天文观测?”如果真是这样,观测点又在哪里呢?
随后,他们用钢架模拟柱缝进行观测,两年间逐步验证了其观测功能。此时,武家璧的回复带来曙光:“这些柱缝的光线似乎交汇于一点,古人会不会就在这个点上观测日出?”一句话如惊雷破晓,指明了方向。
方向已明,剩下的唯有坚持,考古队开始了“逐日之旅”。大半年里,他们一次次站在不同预设的圆心进行不间断测试,终于找到了先民们观象授时的位置 ——向下一挖,便发现了观测点的夯土基址。
这座观象台是夯基石柱与观测圆心共同组成的,是四千年前,先民通过观测初升的阳光穿过不同柱缝后显示节令的授时精密仪器。它凝聚了先民的智慧,证明了古人对时间的掌握,以此指导农事,为后续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作为考古人,何努很荣幸能够参与中华文明的发掘、解码与传承,也相信一铲一刷坚定且持久的考古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。
一位“画家”的陶寺考古四十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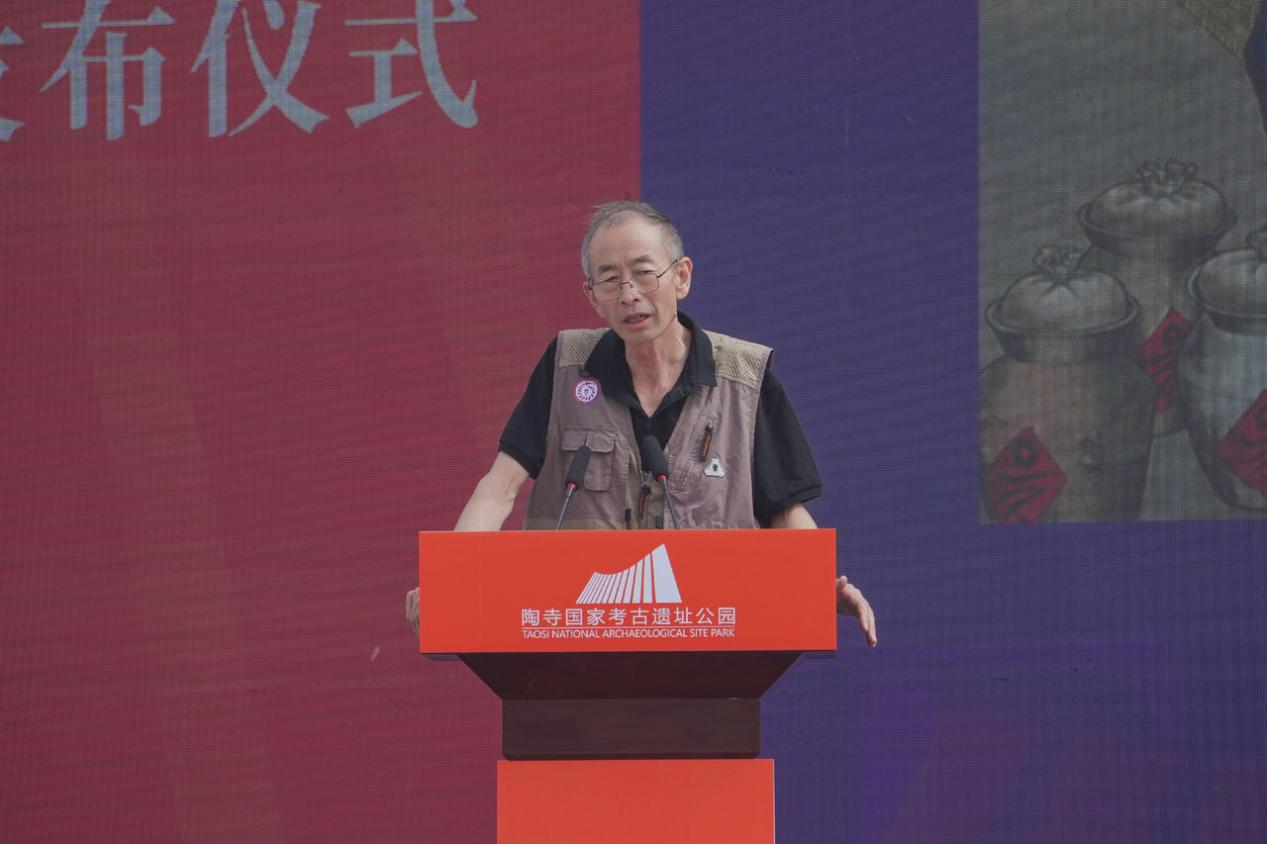
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冯九生,是个地地道道的临汾人。原本他对考古并不感兴趣,更想当个画家。1982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招募会绘图的技术人员,这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了考古工作队的一员,从此与考古和陶寺结下不解之缘。
2002年,在何努队长的带领下,冯九生负责发掘陶寺遗址M22中期大墓。在接近墓底2米时,他一铲子刮过,土层上浮现出一块粉色、像蝴蝶的痕迹。陶寺出土的文物大多是灰色,这让冯九生不敢大意。继续往下发掘,一根有粉红、石绿、烟黑三种颜色色段的漆木杆直立在眼前。
4000多年前的器物仍有如此鲜艳的颜色,直觉告诉冯九生,这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。他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回整理室,用几个月时间一点点清理出这根比他还高的“彩绘漆木杆”。
此后几年,这根漆木杆的用途一直是个谜。直到 2009 年,中国科学院古天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推测其可能与日影测量有关。考古队开始在古籍中找寻答案。
《周髀算经》记载“夏至日晷,尺六寸,即为地中。”冯九生和队员们猜想,这个“彩绘漆木杆”会不会就是测量“地中”的仪器呢?如果是的话,和它配套使用的又是什么呢?他们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墓地出土的另一根漆木杆。
时间到了夏至日,考古队拿着复原的两根漆木杆来到陶寺观象台验证猜想。日影缓缓移动,正午时分,日影定格在漆木杆第11格刻度,现场瞬间沸腾——因为这个刻度长39.9厘米,合陶寺时期的长度为1.6尺,正好印证了古籍中记载的“地中”。
“地中之都、中土之国”,陶寺遗址出土的“彩绘漆木杆”不仅是一个文化符号、王权的象征,也更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向心力。
回首过往,冯九生在发掘陶寺的过程中画了1000多幅图,儿时的画家梦在一次次对陶寺遗址的绘图中得以实现。如今他虽已退休,却仍以顾问身份参与陶寺遗址的保护、发掘和利用工作,在陶寺这个与他生命紧密相连的地方,继续探索与热爱。
我们的根脉与骄傲

70岁的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建录是临汾襄汾人。自小在塔儿山下长大,听老人们讲着当地的故事,让他心里总装着些想不通的“怪事”:为啥大家把太阳叫“尧窝”?清明节的馍馍上为啥总有“蛇娃子”(叫“蛇馍馍”)?当地人们传唱的《击壤歌》,擅长的敲锣打鼓,春种、夏收的时节,还有王云、兴光、小王这些村名,似乎都藏着玄机。
直到陶寺的黄土一层层被揭开,高建录才明白,这些日常念叨的事物,全是老祖宗4000多年前创造的文明。
考古队的铲子挖开的不仅是黄土,也为襄汾人寻回了文明的魂。
作为尧文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,高建录渴望和考古队员一起探索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,弄清“我们从哪里来、怎么来”。陶寺遗址的考古成果,让他看到远古并非蒙昧,而是早已闪烁文明的光彩。
从2004年第一次到来陶寺遗址,二十年间,高建录往陶寺跑了上百趟,走进考古工地看发掘出的宝贝,向专家请教探方和文物中隐藏的文明密码,陪同外地客人参观并讲述陶寺的故事。他还主编出版了《崇山志》《帝尧传说在襄汾》等著作,创作发表了《古中国从这里走来》《塔儿山的光芒》等文章。
如今,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,人们随时能走进这片土地,感受“最初中国”的模样。70岁的他,仍想在有生之年为陶寺多做些事,目前正与朋友撰写《走进陶寺》,想用文学笔法讲述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,让更多人听到陶寺的声音,看到陶寺的气象。
在岁月沉淀中守护文明根脉

陕亚斌是陶寺考古队的“95 后”队员。打记事起,他就常从爷爷奶奶口中听到关于“尧帝”的古老故事,这些传说如同血液流淌在他童年的记忆里。正是这份浓厚的兴趣与热爱,指引他2015年考入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考古发掘专业,踏上探寻文明源头的人生之旅。
大学期间,一张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的灰陶扁壶照片深深震撼了陕亚斌。4000年前的两个朱砂铭文跃然其上,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穿透迷雾,也点燃了他对陶寺、对中华文明源头探索的无限渴望,他与陶寺的故事便从这时开始。
2018年秋天,怀揣着这份渴望,陕亚斌如愿加入陶寺考古队,真正开始了与这片古老热土朝夕相处的发掘工作。
田野考古远不止揭开历史面纱的浪漫与欣喜,更意味着日复一日与自然的角力、与未知的较量,这才是考古人的真实战场——用血肉之躯对抗时间尘埃,用毕生坚守,寻找一个文明的答案。
夜深人静时,疲惫也曾让陕亚斌动摇。但陶寺考古前辈们的身影如明灯,驱散了他心中的迷茫:何努老师在观象台遗址前彻夜推演,用4000年前的日出线印证《尧典》中“历象日月”的记载;高江涛队长二十载扎根黄土,带领他们厘清280万平方米都城的“双城结构”,让“最初中国”的轮廓重现人间;冯九生技师为保护朱书扁壶的朱砂字痕,徒手清理三个月……
“考古如人生,十次落空换一次照亮文明的光。”前辈的教诲在他耳边回响。是啊,没有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执着探索,怎会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豁然开朗?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,需要的正是这份在漫长岁月沉淀中甘于寂寞、百折不挠地守护文明根脉的执着与坚守。
如今,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,这座再现“天文古国”“礼乐之源” 的土地,正将文明火种传递给新一代。陕亚斌深知,前辈的手铲已交到他们的掌心,他们的使命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,以手为尺,丈量文明厚度;以心为炬,点燃探索之光;以志为刃,劈开未知迷雾;用青春与汗水,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探索故事。(王昕妍)









